全国首个用地用海联审项目落地台州 浙江探索“地林草海”审批一次办
全国首个用地用海联审项目落地台州 浙江探索“地林草海”审批一次办
全国首个用地用海联审项目落地台州 浙江探索“地林草海”审批一次办潮新闻客户端(kèhùduān) 张广星
 我和子芳先生是(shì)忘年交文友,他(tā)刚好(gānghǎo)大我二十岁,我1965年生人(shēngrén),那一年他刚参军,他服役的(de)部队是北海舰队,驻地大连。我于(wǒyú)1984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小城工作(gōngzuò)的时候(shíhòu),他刚从部队转业没几年。当时他在(zài)澄江区公所担任秘书,我在黄岩县政府办公室担任秘书,那时我们在工作中(zhōng)就有了接触。我跟的年轻副县长(fùxiànzhǎng)是一位柑橘专家,而当年的澄江区是黄岩蜜橘的最古老又是面积最大的产区。所以当年我就跟着领导跑了澄江区的不少橘园。这时就常碰到子芳先生。又因为在上下级政府办公室同担任秘书工作,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文字交道是比较(bǐjiào)紧密的,需要澄江区在材料上的配合,我总是找子芳先生。子芳先生不仅工作材料写得多且好,他还是个新闻报道的热心人,那时《黄岩报》还没有创刊,而《台州日报(rìbào)》才刚刚创刊,所以他写的报道大多是在黄岩广播站(后来的黄岩人民广播电台)播出,也常被《台州日报》刊出。所以那时的子芳先生文名就有些大。
我和子芳先生是(shì)忘年交文友,他(tā)刚好(gānghǎo)大我二十岁,我1965年生人(shēngrén),那一年他刚参军,他服役的(de)部队是北海舰队,驻地大连。我于(wǒyú)1984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小城工作(gōngzuò)的时候(shíhòu),他刚从部队转业没几年。当时他在(zài)澄江区公所担任秘书,我在黄岩县政府办公室担任秘书,那时我们在工作中(zhōng)就有了接触。我跟的年轻副县长(fùxiànzhǎng)是一位柑橘专家,而当年的澄江区是黄岩蜜橘的最古老又是面积最大的产区。所以当年我就跟着领导跑了澄江区的不少橘园。这时就常碰到子芳先生。又因为在上下级政府办公室同担任秘书工作,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文字交道是比较(bǐjiào)紧密的,需要澄江区在材料上的配合,我总是找子芳先生。子芳先生不仅工作材料写得多且好,他还是个新闻报道的热心人,那时《黄岩报》还没有创刊,而《台州日报(rìbào)》才刚刚创刊,所以他写的报道大多是在黄岩广播站(后来的黄岩人民广播电台)播出,也常被《台州日报》刊出。所以那时的子芳先生文名就有些大。
 当时黄岩广播站在各区公所都派驻有一名记者,这些记者不仅新闻采写(cǎixiě)热情高,而且业务能力也都强,所以区内一般(yìbān)的时政(shízhèng)性(xìng)、事件性新闻,这些大记都不会(búhuì)遗落,但子芳先生依然能被(bèi)评为优秀(yōuxiù)或积极通讯员。他(tā)不跟大记争抢题材,凭着自己在部队里磨练成的新闻敏感,他相信只要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,就不愁没有新闻线索(xīnwénxiànsuǒ)。我记得有一篇让他爆得大名(不仅仅是成名)之作,是《浙江日报(zhèjiāngrìbào)》登出了他采写的报道(bàodào)(bàodào)《武术之乡掀起学武(xuéwǔ)热潮》,有着悠久习武传统的黄岩县澄江区新前乡,因这篇报道一日成名天下知,全省各地武术爱好者赶来新前乡要求拜师学艺。而《浙江日报》刊登的这篇报道,也极大地激发了新前百姓习武的热情。尤其是这个乡的七里村,家家户户本就有“农忙下田务农(wùnóng),农闲习武练拳”的传统,后来新前乡就在七里村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全省(全国?)武术擂台赛。那时我已经到电视台工作,擂台赛现场的盛况,我至今记忆尤新。后来新前乡理所当然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,虽然(suīrán)不能说是这篇报道的功劳,但追根溯源,“始作俑者”,其唯子芳先生乎!
后来我在黄岩电视台当记者,经常自找报道(bàodào)线索,有时就会与子芳先生(xiānshēng)联系,听听他的(de)报道计划。因为他在区公所(qūgōngsuǒ)工作,区公所是一个行政区的领导中枢,各种信息的集散地,掌握着最鲜活(xiānhuó)的新闻线索。我甚至不满足于电话联系,我会骑上自行车去子芳先生的办公(bàngōng)室。这一点也得有个说明:当年的澄江区与县城,就相当于河北省之于北京,在县城的四周(sìzhōu),都是澄江区所属的各个乡。而且澄江区公所办公的院子,就设在县城,离县政府(xiànzhèngfǔ)也只有一箭之地,所以我去子芳先生办公室也很(hěn)方便。我不仅跟子芳(gēnzifāng)先生聊线索,在他忙着的时候,我也会摘下他挂在墙上的全区“工作简报”翻阅。“工作简报”短平快,又(yòu)有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内容,我有时就会从“简报”中获取有价值的、值得进一步深入采访的线索。
所以,我们的(de)交往始于新闻合作。子芳先生给予我的印象,他(tā)就是澄江区的活地图,是狂热的新闻通讯员。
当时黄岩广播站在各区公所都派驻有一名记者,这些记者不仅新闻采写(cǎixiě)热情高,而且业务能力也都强,所以区内一般(yìbān)的时政(shízhèng)性(xìng)、事件性新闻,这些大记都不会(búhuì)遗落,但子芳先生依然能被(bèi)评为优秀(yōuxiù)或积极通讯员。他(tā)不跟大记争抢题材,凭着自己在部队里磨练成的新闻敏感,他相信只要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,就不愁没有新闻线索(xīnwénxiànsuǒ)。我记得有一篇让他爆得大名(不仅仅是成名)之作,是《浙江日报(zhèjiāngrìbào)》登出了他采写的报道(bàodào)(bàodào)《武术之乡掀起学武(xuéwǔ)热潮》,有着悠久习武传统的黄岩县澄江区新前乡,因这篇报道一日成名天下知,全省各地武术爱好者赶来新前乡要求拜师学艺。而《浙江日报》刊登的这篇报道,也极大地激发了新前百姓习武的热情。尤其是这个乡的七里村,家家户户本就有“农忙下田务农(wùnóng),农闲习武练拳”的传统,后来新前乡就在七里村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全省(全国?)武术擂台赛。那时我已经到电视台工作,擂台赛现场的盛况,我至今记忆尤新。后来新前乡理所当然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,虽然(suīrán)不能说是这篇报道的功劳,但追根溯源,“始作俑者”,其唯子芳先生乎!
后来我在黄岩电视台当记者,经常自找报道(bàodào)线索,有时就会与子芳先生(xiānshēng)联系,听听他的(de)报道计划。因为他在区公所(qūgōngsuǒ)工作,区公所是一个行政区的领导中枢,各种信息的集散地,掌握着最鲜活(xiānhuó)的新闻线索。我甚至不满足于电话联系,我会骑上自行车去子芳先生的办公(bàngōng)室。这一点也得有个说明:当年的澄江区与县城,就相当于河北省之于北京,在县城的四周(sìzhōu),都是澄江区所属的各个乡。而且澄江区公所办公的院子,就设在县城,离县政府(xiànzhèngfǔ)也只有一箭之地,所以我去子芳先生办公室也很(hěn)方便。我不仅跟子芳(gēnzifāng)先生聊线索,在他忙着的时候,我也会摘下他挂在墙上的全区“工作简报”翻阅。“工作简报”短平快,又(yòu)有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内容,我有时就会从“简报”中获取有价值的、值得进一步深入采访的线索。
所以,我们的(de)交往始于新闻合作。子芳先生给予我的印象,他(tā)就是澄江区的活地图,是狂热的新闻通讯员。
 后来我走上了地方媒体的(de)管理岗位,自己去(qù)一线采访的机会少了,与子芳先生的联系也就少了。在(zài)三十年前全国实施的撤区扩镇并乡(xiāng)的时候,澄江区公所也被撤掉了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子芳先生竟然(jìngrán)选择了去县审计局,而且竟然担任了审计事务所主任职务。审计事务所是业务性(yèwùxìng)很强的单位,出身(chūshēn)于海军、在区公所担任秘书兼业余通讯员的子芳先生,是怎么胜任审计事务所的责任的呢?我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,并没有直接(zhíjiē)询问子芳先生。直到前年我受托(shòutuō)编辑一本九龙文学院的文集,子芳先生送来一组散文,其中有一篇《我的书房》,道出了他选择去审计部门的原委,让我对子芳先生的学习力更加敬佩:
只有初中文化的我自学读完(dúwán)大学财经管理的书,在海军部队担任(dānrèn)财务助理员,同时指导国防(guófáng)、工业、农业和商业4个(gè)部门不同性质(xìngzhì)的会计业务,因其经验具有指导性,被北海舰队航空兵推广,刊登在1973年6月8日人民海军报上;转业在乡镇任会计辅导员,培训辅导乡、村、组会计出纳的财经业务,因方法别开生面,让我在全县农经大会上介绍具体做法,推广经验;调到审计局,49岁那年考取了审计师职称,担任审计事务所所长期间(qījiān),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(gòngtóngnǔlì),获得台州(tāizhōu)第一、全省十佳之第5佳审计事务所。
后来我走上了地方媒体的(de)管理岗位,自己去(qù)一线采访的机会少了,与子芳先生的联系也就少了。在(zài)三十年前全国实施的撤区扩镇并乡(xiāng)的时候,澄江区公所也被撤掉了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子芳先生竟然(jìngrán)选择了去县审计局,而且竟然担任了审计事务所主任职务。审计事务所是业务性(yèwùxìng)很强的单位,出身(chūshēn)于海军、在区公所担任秘书兼业余通讯员的子芳先生,是怎么胜任审计事务所的责任的呢?我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,并没有直接(zhíjiē)询问子芳先生。直到前年我受托(shòutuō)编辑一本九龙文学院的文集,子芳先生送来一组散文,其中有一篇《我的书房》,道出了他选择去审计部门的原委,让我对子芳先生的学习力更加敬佩:
只有初中文化的我自学读完(dúwán)大学财经管理的书,在海军部队担任(dānrèn)财务助理员,同时指导国防(guófáng)、工业、农业和商业4个(gè)部门不同性质(xìngzhì)的会计业务,因其经验具有指导性,被北海舰队航空兵推广,刊登在1973年6月8日人民海军报上;转业在乡镇任会计辅导员,培训辅导乡、村、组会计出纳的财经业务,因方法别开生面,让我在全县农经大会上介绍具体做法,推广经验;调到审计局,49岁那年考取了审计师职称,担任审计事务所所长期间(qījiān),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(gòngtóngnǔlì),获得台州(tāizhōu)第一、全省十佳之第5佳审计事务所。
 我很(hěn)喜欢子芳先生的《我的书房》一文(yīwén),因为他(tā)也写出了我的心声,我们有着共同的爱书情怀。虽然我们差着二十多年的岁月,从现在社会(shèhuì)的时代演变来看,二十年的变化太大了,太快(tàikuài)了。但(dàn)如果(rúguǒ)倒回去五十年,那时的社会面貌几乎亘古如斯,所以我和(hé)子芳先生年少和年轻(niánqīng)时经历的乡村社会,是非常接近的。我们都(dōu)生活在物质(wùzhì)和文化都很贫乏的偏僻村庄,但我们都对阅读书籍充满着渴望。他回忆,自己1962年初中毕业到1965年参军入伍这三年在村里的务农,虽然干农活很辛苦,但他最感到苦闷难熬的是无书可读。为了能读书,他通过调到县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小学班主任的关系(guānxì),办了一张借(jiè)书卡。但那时他从永宁江北王林乡进城可不容易,需要走三十多分钟到渡口,这里的江面(jiāngmiàn)已经比较宽阔,离海口已经不远了。渡过永宁江后,继续步行十多里路才能赶到城里。每次都借一堆书,白天(báitiān)劳动,晚上苦读(实际也是悦读)。好在村里也有几个与他一样爱阅读的人,他们交换着阅读,并经常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。对于阅读的热爱(rèài),使得子芳先生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受到了成长的锤炼且脱颖而出,被选用为财务助理员,从而埋下(máixià)了他转业之后(zhīhòu)从事乡镇财务管理和后来步入政府审计部门的伏笔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一生对于文字和文学的钟爱之情。
我很(hěn)喜欢子芳先生的《我的书房》一文(yīwén),因为他(tā)也写出了我的心声,我们有着共同的爱书情怀。虽然我们差着二十多年的岁月,从现在社会(shèhuì)的时代演变来看,二十年的变化太大了,太快(tàikuài)了。但(dàn)如果(rúguǒ)倒回去五十年,那时的社会面貌几乎亘古如斯,所以我和(hé)子芳先生年少和年轻(niánqīng)时经历的乡村社会,是非常接近的。我们都(dōu)生活在物质(wùzhì)和文化都很贫乏的偏僻村庄,但我们都对阅读书籍充满着渴望。他回忆,自己1962年初中毕业到1965年参军入伍这三年在村里的务农,虽然干农活很辛苦,但他最感到苦闷难熬的是无书可读。为了能读书,他通过调到县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小学班主任的关系(guānxì),办了一张借(jiè)书卡。但那时他从永宁江北王林乡进城可不容易,需要走三十多分钟到渡口,这里的江面(jiāngmiàn)已经比较宽阔,离海口已经不远了。渡过永宁江后,继续步行十多里路才能赶到城里。每次都借一堆书,白天(báitiān)劳动,晚上苦读(实际也是悦读)。好在村里也有几个与他一样爱阅读的人,他们交换着阅读,并经常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。对于阅读的热爱(rèài),使得子芳先生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受到了成长的锤炼且脱颖而出,被选用为财务助理员,从而埋下(máixià)了他转业之后(zhīhòu)从事乡镇财务管理和后来步入政府审计部门的伏笔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一生对于文字和文学的钟爱之情。
 在(zài)部队这座大熔炉里,阅读不仅增长了他的业务才干,还让他爱(ài)上了写(xiě)作。他另有一篇散文《写信用笺的年代》,谈到了他写作的起步是从军营里写家信开始的。一个南方人到了北方,相隔千里之遥,每逢周末,思乡思亲心切,这个时候,他就铺开信纸,提起笔来,我(wǒ)手写我心,将对亲人(qīnrén)和家乡的深情厚意都(dōu)倾泻在一张又一张纸上。他说,每个(měigè)星期六晚上和整个星期天,都是他的专属写信时间。写完自己的家信后,他再给不识字或识字少不能写信的战友写家信。
现在人(rén)(rén)类的交流工具和交流方式太现代化了(le),太方便了。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打开手机,无论是通话还是微信文字或语音或视频,千里万里之远如当面促膝谈,延续了人类几千年的写纸信(笺)才能沟通的方式,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。但我总觉得(juéde),这是(zhèshì)一种深深的遗憾(yíhàn),因为写纸信是人和人之间(zhījiān)进行深度的情感(qínggǎn)交流、思想沟通的方式。就是在我们中国,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信函都成为了文学名著。我总是觉得,写信也好(yěhǎo),写日记也好,都是文学练笔和积累素材最好的方式。有些年轻的朋友偶尔会向我问起写作上的事情,鉴于写信的方式已经作古,我所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多写日记,每天都写,不然怎么叫日记呢(ne)?
在(zài)部队这座大熔炉里,阅读不仅增长了他的业务才干,还让他爱(ài)上了写(xiě)作。他另有一篇散文《写信用笺的年代》,谈到了他写作的起步是从军营里写家信开始的。一个南方人到了北方,相隔千里之遥,每逢周末,思乡思亲心切,这个时候,他就铺开信纸,提起笔来,我(wǒ)手写我心,将对亲人(qīnrén)和家乡的深情厚意都(dōu)倾泻在一张又一张纸上。他说,每个(měigè)星期六晚上和整个星期天,都是他的专属写信时间。写完自己的家信后,他再给不识字或识字少不能写信的战友写家信。
现在人(rén)(rén)类的交流工具和交流方式太现代化了(le),太方便了。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打开手机,无论是通话还是微信文字或语音或视频,千里万里之远如当面促膝谈,延续了人类几千年的写纸信(笺)才能沟通的方式,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。但我总觉得(juéde),这是(zhèshì)一种深深的遗憾(yíhàn),因为写纸信是人和人之间(zhījiān)进行深度的情感(qínggǎn)交流、思想沟通的方式。就是在我们中国,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信函都成为了文学名著。我总是觉得,写信也好(yěhǎo),写日记也好,都是文学练笔和积累素材最好的方式。有些年轻的朋友偶尔会向我问起写作上的事情,鉴于写信的方式已经作古,我所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多写日记,每天都写,不然怎么叫日记呢(ne)?
 有一些年没有(méiyǒu)见到子芳先生了,也很少看到子芳先生发表出来的作品了。我的工作也离开了黄岩,总是很忙,虽然我还是(háishì)住在(zài)(zài)黄岩,但每天都是在黄岩-椒江两个城区之间奔忙,直到我卸下一线业务(yèwù)的重担进入机关,我才有心思重新融入黄岩的文友圈子。这时我才发现(fāxiàn),已经退了休的子芳先生就像焕发了文学青春一样,在散文创作(chuàngzuò)、古体诗词创作上激情勃发,佳作频出。在台州和黄岩两级的各种(gèzhǒng)纸媒上,经常读到他的真挚朴实的散文作品。但他创作和发表得更多的是古体诗词创作。他成为了黄岩诗坛的重要人物(rénwù),在很多的文学采风现场,都有他活动的身影。
有一些年没有(méiyǒu)见到子芳先生了,也很少看到子芳先生发表出来的作品了。我的工作也离开了黄岩,总是很忙,虽然我还是(háishì)住在(zài)(zài)黄岩,但每天都是在黄岩-椒江两个城区之间奔忙,直到我卸下一线业务(yèwù)的重担进入机关,我才有心思重新融入黄岩的文友圈子。这时我才发现(fāxiàn),已经退了休的子芳先生就像焕发了文学青春一样,在散文创作(chuàngzuò)、古体诗词创作上激情勃发,佳作频出。在台州和黄岩两级的各种(gèzhǒng)纸媒上,经常读到他的真挚朴实的散文作品。但他创作和发表得更多的是古体诗词创作。他成为了黄岩诗坛的重要人物(rénwù),在很多的文学采风现场,都有他活动的身影。
 我们又(yòu)走在了一起。子芳先生受九龙文学院(wénxuéyuàn)院长叶廷璧的委托,执行主编《九龙诗词》刊物,而我忝(tiǎn)为九龙文学院的执行院长,虽然我不写古体诗(gǔtǐshī)词,但子芳先生编出新的一期之后,叶院长总会召集子芳先生和另一位编辑以及一些骨干作者,边喝酒边谈诗。有时子芳先生也(yě)会派(huìpài)我写小序之类的文字活。我总是抹不开面子,明知(míngzhī)写不好,也只好应承下来。子芳先生才高而德厚,温良恭俭让,乃谦谦君子,恂恂儒者,所以没有人会驳他的面子。
我们又(yòu)走在了一起。子芳先生受九龙文学院(wénxuéyuàn)院长叶廷璧的委托,执行主编《九龙诗词》刊物,而我忝(tiǎn)为九龙文学院的执行院长,虽然我不写古体诗(gǔtǐshī)词,但子芳先生编出新的一期之后,叶院长总会召集子芳先生和另一位编辑以及一些骨干作者,边喝酒边谈诗。有时子芳先生也(yě)会派(huìpài)我写小序之类的文字活。我总是抹不开面子,明知(míngzhī)写不好,也只好应承下来。子芳先生才高而德厚,温良恭俭让,乃谦谦君子,恂恂儒者,所以没有人会驳他的面子。
 今逢子芳先生八十大寿,无以为贺,聊写我与他四十多年的(de)交往点滴以及所得的印象(yìnxiàng),谨祝子芳先生福寿绵长,创作健旺!
今逢子芳先生八十大寿,无以为贺,聊写我与他四十多年的(de)交往点滴以及所得的印象(yìnxiàng),谨祝子芳先生福寿绵长,创作健旺!
潮新闻客户端(kèhùduān) 张广星
 我和子芳先生是(shì)忘年交文友,他(tā)刚好(gānghǎo)大我二十岁,我1965年生人(shēngrén),那一年他刚参军,他服役的(de)部队是北海舰队,驻地大连。我于(wǒyú)1984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小城工作(gōngzuò)的时候(shíhòu),他刚从部队转业没几年。当时他在(zài)澄江区公所担任秘书,我在黄岩县政府办公室担任秘书,那时我们在工作中(zhōng)就有了接触。我跟的年轻副县长(fùxiànzhǎng)是一位柑橘专家,而当年的澄江区是黄岩蜜橘的最古老又是面积最大的产区。所以当年我就跟着领导跑了澄江区的不少橘园。这时就常碰到子芳先生。又因为在上下级政府办公室同担任秘书工作,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文字交道是比较(bǐjiào)紧密的,需要澄江区在材料上的配合,我总是找子芳先生。子芳先生不仅工作材料写得多且好,他还是个新闻报道的热心人,那时《黄岩报》还没有创刊,而《台州日报(rìbào)》才刚刚创刊,所以他写的报道大多是在黄岩广播站(后来的黄岩人民广播电台)播出,也常被《台州日报》刊出。所以那时的子芳先生文名就有些大。
我和子芳先生是(shì)忘年交文友,他(tā)刚好(gānghǎo)大我二十岁,我1965年生人(shēngrén),那一年他刚参军,他服役的(de)部队是北海舰队,驻地大连。我于(wǒyú)1984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小城工作(gōngzuò)的时候(shíhòu),他刚从部队转业没几年。当时他在(zài)澄江区公所担任秘书,我在黄岩县政府办公室担任秘书,那时我们在工作中(zhōng)就有了接触。我跟的年轻副县长(fùxiànzhǎng)是一位柑橘专家,而当年的澄江区是黄岩蜜橘的最古老又是面积最大的产区。所以当年我就跟着领导跑了澄江区的不少橘园。这时就常碰到子芳先生。又因为在上下级政府办公室同担任秘书工作,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文字交道是比较(bǐjiào)紧密的,需要澄江区在材料上的配合,我总是找子芳先生。子芳先生不仅工作材料写得多且好,他还是个新闻报道的热心人,那时《黄岩报》还没有创刊,而《台州日报(rìbào)》才刚刚创刊,所以他写的报道大多是在黄岩广播站(后来的黄岩人民广播电台)播出,也常被《台州日报》刊出。所以那时的子芳先生文名就有些大。
 当时黄岩广播站在各区公所都派驻有一名记者,这些记者不仅新闻采写(cǎixiě)热情高,而且业务能力也都强,所以区内一般(yìbān)的时政(shízhèng)性(xìng)、事件性新闻,这些大记都不会(búhuì)遗落,但子芳先生依然能被(bèi)评为优秀(yōuxiù)或积极通讯员。他(tā)不跟大记争抢题材,凭着自己在部队里磨练成的新闻敏感,他相信只要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,就不愁没有新闻线索(xīnwénxiànsuǒ)。我记得有一篇让他爆得大名(不仅仅是成名)之作,是《浙江日报(zhèjiāngrìbào)》登出了他采写的报道(bàodào)(bàodào)《武术之乡掀起学武(xuéwǔ)热潮》,有着悠久习武传统的黄岩县澄江区新前乡,因这篇报道一日成名天下知,全省各地武术爱好者赶来新前乡要求拜师学艺。而《浙江日报》刊登的这篇报道,也极大地激发了新前百姓习武的热情。尤其是这个乡的七里村,家家户户本就有“农忙下田务农(wùnóng),农闲习武练拳”的传统,后来新前乡就在七里村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全省(全国?)武术擂台赛。那时我已经到电视台工作,擂台赛现场的盛况,我至今记忆尤新。后来新前乡理所当然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,虽然(suīrán)不能说是这篇报道的功劳,但追根溯源,“始作俑者”,其唯子芳先生乎!
后来我在黄岩电视台当记者,经常自找报道(bàodào)线索,有时就会与子芳先生(xiānshēng)联系,听听他的(de)报道计划。因为他在区公所(qūgōngsuǒ)工作,区公所是一个行政区的领导中枢,各种信息的集散地,掌握着最鲜活(xiānhuó)的新闻线索。我甚至不满足于电话联系,我会骑上自行车去子芳先生的办公(bàngōng)室。这一点也得有个说明:当年的澄江区与县城,就相当于河北省之于北京,在县城的四周(sìzhōu),都是澄江区所属的各个乡。而且澄江区公所办公的院子,就设在县城,离县政府(xiànzhèngfǔ)也只有一箭之地,所以我去子芳先生办公室也很(hěn)方便。我不仅跟子芳(gēnzifāng)先生聊线索,在他忙着的时候,我也会摘下他挂在墙上的全区“工作简报”翻阅。“工作简报”短平快,又(yòu)有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内容,我有时就会从“简报”中获取有价值的、值得进一步深入采访的线索。
所以,我们的(de)交往始于新闻合作。子芳先生给予我的印象,他(tā)就是澄江区的活地图,是狂热的新闻通讯员。
当时黄岩广播站在各区公所都派驻有一名记者,这些记者不仅新闻采写(cǎixiě)热情高,而且业务能力也都强,所以区内一般(yìbān)的时政(shízhèng)性(xìng)、事件性新闻,这些大记都不会(búhuì)遗落,但子芳先生依然能被(bèi)评为优秀(yōuxiù)或积极通讯员。他(tā)不跟大记争抢题材,凭着自己在部队里磨练成的新闻敏感,他相信只要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,就不愁没有新闻线索(xīnwénxiànsuǒ)。我记得有一篇让他爆得大名(不仅仅是成名)之作,是《浙江日报(zhèjiāngrìbào)》登出了他采写的报道(bàodào)(bàodào)《武术之乡掀起学武(xuéwǔ)热潮》,有着悠久习武传统的黄岩县澄江区新前乡,因这篇报道一日成名天下知,全省各地武术爱好者赶来新前乡要求拜师学艺。而《浙江日报》刊登的这篇报道,也极大地激发了新前百姓习武的热情。尤其是这个乡的七里村,家家户户本就有“农忙下田务农(wùnóng),农闲习武练拳”的传统,后来新前乡就在七里村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全省(全国?)武术擂台赛。那时我已经到电视台工作,擂台赛现场的盛况,我至今记忆尤新。后来新前乡理所当然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,虽然(suīrán)不能说是这篇报道的功劳,但追根溯源,“始作俑者”,其唯子芳先生乎!
后来我在黄岩电视台当记者,经常自找报道(bàodào)线索,有时就会与子芳先生(xiānshēng)联系,听听他的(de)报道计划。因为他在区公所(qūgōngsuǒ)工作,区公所是一个行政区的领导中枢,各种信息的集散地,掌握着最鲜活(xiānhuó)的新闻线索。我甚至不满足于电话联系,我会骑上自行车去子芳先生的办公(bàngōng)室。这一点也得有个说明:当年的澄江区与县城,就相当于河北省之于北京,在县城的四周(sìzhōu),都是澄江区所属的各个乡。而且澄江区公所办公的院子,就设在县城,离县政府(xiànzhèngfǔ)也只有一箭之地,所以我去子芳先生办公室也很(hěn)方便。我不仅跟子芳(gēnzifāng)先生聊线索,在他忙着的时候,我也会摘下他挂在墙上的全区“工作简报”翻阅。“工作简报”短平快,又(yòu)有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内容,我有时就会从“简报”中获取有价值的、值得进一步深入采访的线索。
所以,我们的(de)交往始于新闻合作。子芳先生给予我的印象,他(tā)就是澄江区的活地图,是狂热的新闻通讯员。
 后来我走上了地方媒体的(de)管理岗位,自己去(qù)一线采访的机会少了,与子芳先生的联系也就少了。在(zài)三十年前全国实施的撤区扩镇并乡(xiāng)的时候,澄江区公所也被撤掉了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子芳先生竟然(jìngrán)选择了去县审计局,而且竟然担任了审计事务所主任职务。审计事务所是业务性(yèwùxìng)很强的单位,出身(chūshēn)于海军、在区公所担任秘书兼业余通讯员的子芳先生,是怎么胜任审计事务所的责任的呢?我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,并没有直接(zhíjiē)询问子芳先生。直到前年我受托(shòutuō)编辑一本九龙文学院的文集,子芳先生送来一组散文,其中有一篇《我的书房》,道出了他选择去审计部门的原委,让我对子芳先生的学习力更加敬佩:
只有初中文化的我自学读完(dúwán)大学财经管理的书,在海军部队担任(dānrèn)财务助理员,同时指导国防(guófáng)、工业、农业和商业4个(gè)部门不同性质(xìngzhì)的会计业务,因其经验具有指导性,被北海舰队航空兵推广,刊登在1973年6月8日人民海军报上;转业在乡镇任会计辅导员,培训辅导乡、村、组会计出纳的财经业务,因方法别开生面,让我在全县农经大会上介绍具体做法,推广经验;调到审计局,49岁那年考取了审计师职称,担任审计事务所所长期间(qījiān),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(gòngtóngnǔlì),获得台州(tāizhōu)第一、全省十佳之第5佳审计事务所。
后来我走上了地方媒体的(de)管理岗位,自己去(qù)一线采访的机会少了,与子芳先生的联系也就少了。在(zài)三十年前全国实施的撤区扩镇并乡(xiāng)的时候,澄江区公所也被撤掉了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子芳先生竟然(jìngrán)选择了去县审计局,而且竟然担任了审计事务所主任职务。审计事务所是业务性(yèwùxìng)很强的单位,出身(chūshēn)于海军、在区公所担任秘书兼业余通讯员的子芳先生,是怎么胜任审计事务所的责任的呢?我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,并没有直接(zhíjiē)询问子芳先生。直到前年我受托(shòutuō)编辑一本九龙文学院的文集,子芳先生送来一组散文,其中有一篇《我的书房》,道出了他选择去审计部门的原委,让我对子芳先生的学习力更加敬佩:
只有初中文化的我自学读完(dúwán)大学财经管理的书,在海军部队担任(dānrèn)财务助理员,同时指导国防(guófáng)、工业、农业和商业4个(gè)部门不同性质(xìngzhì)的会计业务,因其经验具有指导性,被北海舰队航空兵推广,刊登在1973年6月8日人民海军报上;转业在乡镇任会计辅导员,培训辅导乡、村、组会计出纳的财经业务,因方法别开生面,让我在全县农经大会上介绍具体做法,推广经验;调到审计局,49岁那年考取了审计师职称,担任审计事务所所长期间(qījiān),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(gòngtóngnǔlì),获得台州(tāizhōu)第一、全省十佳之第5佳审计事务所。
 我很(hěn)喜欢子芳先生的《我的书房》一文(yīwén),因为他(tā)也写出了我的心声,我们有着共同的爱书情怀。虽然我们差着二十多年的岁月,从现在社会(shèhuì)的时代演变来看,二十年的变化太大了,太快(tàikuài)了。但(dàn)如果(rúguǒ)倒回去五十年,那时的社会面貌几乎亘古如斯,所以我和(hé)子芳先生年少和年轻(niánqīng)时经历的乡村社会,是非常接近的。我们都(dōu)生活在物质(wùzhì)和文化都很贫乏的偏僻村庄,但我们都对阅读书籍充满着渴望。他回忆,自己1962年初中毕业到1965年参军入伍这三年在村里的务农,虽然干农活很辛苦,但他最感到苦闷难熬的是无书可读。为了能读书,他通过调到县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小学班主任的关系(guānxì),办了一张借(jiè)书卡。但那时他从永宁江北王林乡进城可不容易,需要走三十多分钟到渡口,这里的江面(jiāngmiàn)已经比较宽阔,离海口已经不远了。渡过永宁江后,继续步行十多里路才能赶到城里。每次都借一堆书,白天(báitiān)劳动,晚上苦读(实际也是悦读)。好在村里也有几个与他一样爱阅读的人,他们交换着阅读,并经常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。对于阅读的热爱(rèài),使得子芳先生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受到了成长的锤炼且脱颖而出,被选用为财务助理员,从而埋下(máixià)了他转业之后(zhīhòu)从事乡镇财务管理和后来步入政府审计部门的伏笔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一生对于文字和文学的钟爱之情。
我很(hěn)喜欢子芳先生的《我的书房》一文(yīwén),因为他(tā)也写出了我的心声,我们有着共同的爱书情怀。虽然我们差着二十多年的岁月,从现在社会(shèhuì)的时代演变来看,二十年的变化太大了,太快(tàikuài)了。但(dàn)如果(rúguǒ)倒回去五十年,那时的社会面貌几乎亘古如斯,所以我和(hé)子芳先生年少和年轻(niánqīng)时经历的乡村社会,是非常接近的。我们都(dōu)生活在物质(wùzhì)和文化都很贫乏的偏僻村庄,但我们都对阅读书籍充满着渴望。他回忆,自己1962年初中毕业到1965年参军入伍这三年在村里的务农,虽然干农活很辛苦,但他最感到苦闷难熬的是无书可读。为了能读书,他通过调到县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小学班主任的关系(guānxì),办了一张借(jiè)书卡。但那时他从永宁江北王林乡进城可不容易,需要走三十多分钟到渡口,这里的江面(jiāngmiàn)已经比较宽阔,离海口已经不远了。渡过永宁江后,继续步行十多里路才能赶到城里。每次都借一堆书,白天(báitiān)劳动,晚上苦读(实际也是悦读)。好在村里也有几个与他一样爱阅读的人,他们交换着阅读,并经常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。对于阅读的热爱(rèài),使得子芳先生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受到了成长的锤炼且脱颖而出,被选用为财务助理员,从而埋下(máixià)了他转业之后(zhīhòu)从事乡镇财务管理和后来步入政府审计部门的伏笔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一生对于文字和文学的钟爱之情。
 在(zài)部队这座大熔炉里,阅读不仅增长了他的业务才干,还让他爱(ài)上了写(xiě)作。他另有一篇散文《写信用笺的年代》,谈到了他写作的起步是从军营里写家信开始的。一个南方人到了北方,相隔千里之遥,每逢周末,思乡思亲心切,这个时候,他就铺开信纸,提起笔来,我(wǒ)手写我心,将对亲人(qīnrén)和家乡的深情厚意都(dōu)倾泻在一张又一张纸上。他说,每个(měigè)星期六晚上和整个星期天,都是他的专属写信时间。写完自己的家信后,他再给不识字或识字少不能写信的战友写家信。
现在人(rén)(rén)类的交流工具和交流方式太现代化了(le),太方便了。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打开手机,无论是通话还是微信文字或语音或视频,千里万里之远如当面促膝谈,延续了人类几千年的写纸信(笺)才能沟通的方式,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。但我总觉得(juéde),这是(zhèshì)一种深深的遗憾(yíhàn),因为写纸信是人和人之间(zhījiān)进行深度的情感(qínggǎn)交流、思想沟通的方式。就是在我们中国,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信函都成为了文学名著。我总是觉得,写信也好(yěhǎo),写日记也好,都是文学练笔和积累素材最好的方式。有些年轻的朋友偶尔会向我问起写作上的事情,鉴于写信的方式已经作古,我所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多写日记,每天都写,不然怎么叫日记呢(ne)?
在(zài)部队这座大熔炉里,阅读不仅增长了他的业务才干,还让他爱(ài)上了写(xiě)作。他另有一篇散文《写信用笺的年代》,谈到了他写作的起步是从军营里写家信开始的。一个南方人到了北方,相隔千里之遥,每逢周末,思乡思亲心切,这个时候,他就铺开信纸,提起笔来,我(wǒ)手写我心,将对亲人(qīnrén)和家乡的深情厚意都(dōu)倾泻在一张又一张纸上。他说,每个(měigè)星期六晚上和整个星期天,都是他的专属写信时间。写完自己的家信后,他再给不识字或识字少不能写信的战友写家信。
现在人(rén)(rén)类的交流工具和交流方式太现代化了(le),太方便了。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打开手机,无论是通话还是微信文字或语音或视频,千里万里之远如当面促膝谈,延续了人类几千年的写纸信(笺)才能沟通的方式,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。但我总觉得(juéde),这是(zhèshì)一种深深的遗憾(yíhàn),因为写纸信是人和人之间(zhījiān)进行深度的情感(qínggǎn)交流、思想沟通的方式。就是在我们中国,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信函都成为了文学名著。我总是觉得,写信也好(yěhǎo),写日记也好,都是文学练笔和积累素材最好的方式。有些年轻的朋友偶尔会向我问起写作上的事情,鉴于写信的方式已经作古,我所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多写日记,每天都写,不然怎么叫日记呢(ne)?
 有一些年没有(méiyǒu)见到子芳先生了,也很少看到子芳先生发表出来的作品了。我的工作也离开了黄岩,总是很忙,虽然我还是(háishì)住在(zài)(zài)黄岩,但每天都是在黄岩-椒江两个城区之间奔忙,直到我卸下一线业务(yèwù)的重担进入机关,我才有心思重新融入黄岩的文友圈子。这时我才发现(fāxiàn),已经退了休的子芳先生就像焕发了文学青春一样,在散文创作(chuàngzuò)、古体诗词创作上激情勃发,佳作频出。在台州和黄岩两级的各种(gèzhǒng)纸媒上,经常读到他的真挚朴实的散文作品。但他创作和发表得更多的是古体诗词创作。他成为了黄岩诗坛的重要人物(rénwù),在很多的文学采风现场,都有他活动的身影。
有一些年没有(méiyǒu)见到子芳先生了,也很少看到子芳先生发表出来的作品了。我的工作也离开了黄岩,总是很忙,虽然我还是(háishì)住在(zài)(zài)黄岩,但每天都是在黄岩-椒江两个城区之间奔忙,直到我卸下一线业务(yèwù)的重担进入机关,我才有心思重新融入黄岩的文友圈子。这时我才发现(fāxiàn),已经退了休的子芳先生就像焕发了文学青春一样,在散文创作(chuàngzuò)、古体诗词创作上激情勃发,佳作频出。在台州和黄岩两级的各种(gèzhǒng)纸媒上,经常读到他的真挚朴实的散文作品。但他创作和发表得更多的是古体诗词创作。他成为了黄岩诗坛的重要人物(rénwù),在很多的文学采风现场,都有他活动的身影。
 我们又(yòu)走在了一起。子芳先生受九龙文学院(wénxuéyuàn)院长叶廷璧的委托,执行主编《九龙诗词》刊物,而我忝(tiǎn)为九龙文学院的执行院长,虽然我不写古体诗(gǔtǐshī)词,但子芳先生编出新的一期之后,叶院长总会召集子芳先生和另一位编辑以及一些骨干作者,边喝酒边谈诗。有时子芳先生也(yě)会派(huìpài)我写小序之类的文字活。我总是抹不开面子,明知(míngzhī)写不好,也只好应承下来。子芳先生才高而德厚,温良恭俭让,乃谦谦君子,恂恂儒者,所以没有人会驳他的面子。
我们又(yòu)走在了一起。子芳先生受九龙文学院(wénxuéyuàn)院长叶廷璧的委托,执行主编《九龙诗词》刊物,而我忝(tiǎn)为九龙文学院的执行院长,虽然我不写古体诗(gǔtǐshī)词,但子芳先生编出新的一期之后,叶院长总会召集子芳先生和另一位编辑以及一些骨干作者,边喝酒边谈诗。有时子芳先生也(yě)会派(huìpài)我写小序之类的文字活。我总是抹不开面子,明知(míngzhī)写不好,也只好应承下来。子芳先生才高而德厚,温良恭俭让,乃谦谦君子,恂恂儒者,所以没有人会驳他的面子。
 今逢子芳先生八十大寿,无以为贺,聊写我与他四十多年的(de)交往点滴以及所得的印象(yìnxiàng),谨祝子芳先生福寿绵长,创作健旺!
今逢子芳先生八十大寿,无以为贺,聊写我与他四十多年的(de)交往点滴以及所得的印象(yìnxiàng),谨祝子芳先生福寿绵长,创作健旺!
 我和子芳先生是(shì)忘年交文友,他(tā)刚好(gānghǎo)大我二十岁,我1965年生人(shēngrén),那一年他刚参军,他服役的(de)部队是北海舰队,驻地大连。我于(wǒyú)1984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小城工作(gōngzuò)的时候(shíhòu),他刚从部队转业没几年。当时他在(zài)澄江区公所担任秘书,我在黄岩县政府办公室担任秘书,那时我们在工作中(zhōng)就有了接触。我跟的年轻副县长(fùxiànzhǎng)是一位柑橘专家,而当年的澄江区是黄岩蜜橘的最古老又是面积最大的产区。所以当年我就跟着领导跑了澄江区的不少橘园。这时就常碰到子芳先生。又因为在上下级政府办公室同担任秘书工作,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文字交道是比较(bǐjiào)紧密的,需要澄江区在材料上的配合,我总是找子芳先生。子芳先生不仅工作材料写得多且好,他还是个新闻报道的热心人,那时《黄岩报》还没有创刊,而《台州日报(rìbào)》才刚刚创刊,所以他写的报道大多是在黄岩广播站(后来的黄岩人民广播电台)播出,也常被《台州日报》刊出。所以那时的子芳先生文名就有些大。
我和子芳先生是(shì)忘年交文友,他(tā)刚好(gānghǎo)大我二十岁,我1965年生人(shēngrén),那一年他刚参军,他服役的(de)部队是北海舰队,驻地大连。我于(wǒyú)1984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小城工作(gōngzuò)的时候(shíhòu),他刚从部队转业没几年。当时他在(zài)澄江区公所担任秘书,我在黄岩县政府办公室担任秘书,那时我们在工作中(zhōng)就有了接触。我跟的年轻副县长(fùxiànzhǎng)是一位柑橘专家,而当年的澄江区是黄岩蜜橘的最古老又是面积最大的产区。所以当年我就跟着领导跑了澄江区的不少橘园。这时就常碰到子芳先生。又因为在上下级政府办公室同担任秘书工作,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文字交道是比较(bǐjiào)紧密的,需要澄江区在材料上的配合,我总是找子芳先生。子芳先生不仅工作材料写得多且好,他还是个新闻报道的热心人,那时《黄岩报》还没有创刊,而《台州日报(rìbào)》才刚刚创刊,所以他写的报道大多是在黄岩广播站(后来的黄岩人民广播电台)播出,也常被《台州日报》刊出。所以那时的子芳先生文名就有些大。
 当时黄岩广播站在各区公所都派驻有一名记者,这些记者不仅新闻采写(cǎixiě)热情高,而且业务能力也都强,所以区内一般(yìbān)的时政(shízhèng)性(xìng)、事件性新闻,这些大记都不会(búhuì)遗落,但子芳先生依然能被(bèi)评为优秀(yōuxiù)或积极通讯员。他(tā)不跟大记争抢题材,凭着自己在部队里磨练成的新闻敏感,他相信只要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,就不愁没有新闻线索(xīnwénxiànsuǒ)。我记得有一篇让他爆得大名(不仅仅是成名)之作,是《浙江日报(zhèjiāngrìbào)》登出了他采写的报道(bàodào)(bàodào)《武术之乡掀起学武(xuéwǔ)热潮》,有着悠久习武传统的黄岩县澄江区新前乡,因这篇报道一日成名天下知,全省各地武术爱好者赶来新前乡要求拜师学艺。而《浙江日报》刊登的这篇报道,也极大地激发了新前百姓习武的热情。尤其是这个乡的七里村,家家户户本就有“农忙下田务农(wùnóng),农闲习武练拳”的传统,后来新前乡就在七里村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全省(全国?)武术擂台赛。那时我已经到电视台工作,擂台赛现场的盛况,我至今记忆尤新。后来新前乡理所当然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,虽然(suīrán)不能说是这篇报道的功劳,但追根溯源,“始作俑者”,其唯子芳先生乎!
后来我在黄岩电视台当记者,经常自找报道(bàodào)线索,有时就会与子芳先生(xiānshēng)联系,听听他的(de)报道计划。因为他在区公所(qūgōngsuǒ)工作,区公所是一个行政区的领导中枢,各种信息的集散地,掌握着最鲜活(xiānhuó)的新闻线索。我甚至不满足于电话联系,我会骑上自行车去子芳先生的办公(bàngōng)室。这一点也得有个说明:当年的澄江区与县城,就相当于河北省之于北京,在县城的四周(sìzhōu),都是澄江区所属的各个乡。而且澄江区公所办公的院子,就设在县城,离县政府(xiànzhèngfǔ)也只有一箭之地,所以我去子芳先生办公室也很(hěn)方便。我不仅跟子芳(gēnzifāng)先生聊线索,在他忙着的时候,我也会摘下他挂在墙上的全区“工作简报”翻阅。“工作简报”短平快,又(yòu)有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内容,我有时就会从“简报”中获取有价值的、值得进一步深入采访的线索。
所以,我们的(de)交往始于新闻合作。子芳先生给予我的印象,他(tā)就是澄江区的活地图,是狂热的新闻通讯员。
当时黄岩广播站在各区公所都派驻有一名记者,这些记者不仅新闻采写(cǎixiě)热情高,而且业务能力也都强,所以区内一般(yìbān)的时政(shízhèng)性(xìng)、事件性新闻,这些大记都不会(búhuì)遗落,但子芳先生依然能被(bèi)评为优秀(yōuxiù)或积极通讯员。他(tā)不跟大记争抢题材,凭着自己在部队里磨练成的新闻敏感,他相信只要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,就不愁没有新闻线索(xīnwénxiànsuǒ)。我记得有一篇让他爆得大名(不仅仅是成名)之作,是《浙江日报(zhèjiāngrìbào)》登出了他采写的报道(bàodào)(bàodào)《武术之乡掀起学武(xuéwǔ)热潮》,有着悠久习武传统的黄岩县澄江区新前乡,因这篇报道一日成名天下知,全省各地武术爱好者赶来新前乡要求拜师学艺。而《浙江日报》刊登的这篇报道,也极大地激发了新前百姓习武的热情。尤其是这个乡的七里村,家家户户本就有“农忙下田务农(wùnóng),农闲习武练拳”的传统,后来新前乡就在七里村连续举办了好几届的全省(全国?)武术擂台赛。那时我已经到电视台工作,擂台赛现场的盛况,我至今记忆尤新。后来新前乡理所当然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,虽然(suīrán)不能说是这篇报道的功劳,但追根溯源,“始作俑者”,其唯子芳先生乎!
后来我在黄岩电视台当记者,经常自找报道(bàodào)线索,有时就会与子芳先生(xiānshēng)联系,听听他的(de)报道计划。因为他在区公所(qūgōngsuǒ)工作,区公所是一个行政区的领导中枢,各种信息的集散地,掌握着最鲜活(xiānhuó)的新闻线索。我甚至不满足于电话联系,我会骑上自行车去子芳先生的办公(bàngōng)室。这一点也得有个说明:当年的澄江区与县城,就相当于河北省之于北京,在县城的四周(sìzhōu),都是澄江区所属的各个乡。而且澄江区公所办公的院子,就设在县城,离县政府(xiànzhèngfǔ)也只有一箭之地,所以我去子芳先生办公室也很(hěn)方便。我不仅跟子芳(gēnzifāng)先生聊线索,在他忙着的时候,我也会摘下他挂在墙上的全区“工作简报”翻阅。“工作简报”短平快,又(yòu)有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内容,我有时就会从“简报”中获取有价值的、值得进一步深入采访的线索。
所以,我们的(de)交往始于新闻合作。子芳先生给予我的印象,他(tā)就是澄江区的活地图,是狂热的新闻通讯员。
 后来我走上了地方媒体的(de)管理岗位,自己去(qù)一线采访的机会少了,与子芳先生的联系也就少了。在(zài)三十年前全国实施的撤区扩镇并乡(xiāng)的时候,澄江区公所也被撤掉了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子芳先生竟然(jìngrán)选择了去县审计局,而且竟然担任了审计事务所主任职务。审计事务所是业务性(yèwùxìng)很强的单位,出身(chūshēn)于海军、在区公所担任秘书兼业余通讯员的子芳先生,是怎么胜任审计事务所的责任的呢?我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,并没有直接(zhíjiē)询问子芳先生。直到前年我受托(shòutuō)编辑一本九龙文学院的文集,子芳先生送来一组散文,其中有一篇《我的书房》,道出了他选择去审计部门的原委,让我对子芳先生的学习力更加敬佩:
只有初中文化的我自学读完(dúwán)大学财经管理的书,在海军部队担任(dānrèn)财务助理员,同时指导国防(guófáng)、工业、农业和商业4个(gè)部门不同性质(xìngzhì)的会计业务,因其经验具有指导性,被北海舰队航空兵推广,刊登在1973年6月8日人民海军报上;转业在乡镇任会计辅导员,培训辅导乡、村、组会计出纳的财经业务,因方法别开生面,让我在全县农经大会上介绍具体做法,推广经验;调到审计局,49岁那年考取了审计师职称,担任审计事务所所长期间(qījiān),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(gòngtóngnǔlì),获得台州(tāizhōu)第一、全省十佳之第5佳审计事务所。
后来我走上了地方媒体的(de)管理岗位,自己去(qù)一线采访的机会少了,与子芳先生的联系也就少了。在(zài)三十年前全国实施的撤区扩镇并乡(xiāng)的时候,澄江区公所也被撤掉了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子芳先生竟然(jìngrán)选择了去县审计局,而且竟然担任了审计事务所主任职务。审计事务所是业务性(yèwùxìng)很强的单位,出身(chūshēn)于海军、在区公所担任秘书兼业余通讯员的子芳先生,是怎么胜任审计事务所的责任的呢?我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,并没有直接(zhíjiē)询问子芳先生。直到前年我受托(shòutuō)编辑一本九龙文学院的文集,子芳先生送来一组散文,其中有一篇《我的书房》,道出了他选择去审计部门的原委,让我对子芳先生的学习力更加敬佩:
只有初中文化的我自学读完(dúwán)大学财经管理的书,在海军部队担任(dānrèn)财务助理员,同时指导国防(guófáng)、工业、农业和商业4个(gè)部门不同性质(xìngzhì)的会计业务,因其经验具有指导性,被北海舰队航空兵推广,刊登在1973年6月8日人民海军报上;转业在乡镇任会计辅导员,培训辅导乡、村、组会计出纳的财经业务,因方法别开生面,让我在全县农经大会上介绍具体做法,推广经验;调到审计局,49岁那年考取了审计师职称,担任审计事务所所长期间(qījiān),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(gòngtóngnǔlì),获得台州(tāizhōu)第一、全省十佳之第5佳审计事务所。
 我很(hěn)喜欢子芳先生的《我的书房》一文(yīwén),因为他(tā)也写出了我的心声,我们有着共同的爱书情怀。虽然我们差着二十多年的岁月,从现在社会(shèhuì)的时代演变来看,二十年的变化太大了,太快(tàikuài)了。但(dàn)如果(rúguǒ)倒回去五十年,那时的社会面貌几乎亘古如斯,所以我和(hé)子芳先生年少和年轻(niánqīng)时经历的乡村社会,是非常接近的。我们都(dōu)生活在物质(wùzhì)和文化都很贫乏的偏僻村庄,但我们都对阅读书籍充满着渴望。他回忆,自己1962年初中毕业到1965年参军入伍这三年在村里的务农,虽然干农活很辛苦,但他最感到苦闷难熬的是无书可读。为了能读书,他通过调到县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小学班主任的关系(guānxì),办了一张借(jiè)书卡。但那时他从永宁江北王林乡进城可不容易,需要走三十多分钟到渡口,这里的江面(jiāngmiàn)已经比较宽阔,离海口已经不远了。渡过永宁江后,继续步行十多里路才能赶到城里。每次都借一堆书,白天(báitiān)劳动,晚上苦读(实际也是悦读)。好在村里也有几个与他一样爱阅读的人,他们交换着阅读,并经常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。对于阅读的热爱(rèài),使得子芳先生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受到了成长的锤炼且脱颖而出,被选用为财务助理员,从而埋下(máixià)了他转业之后(zhīhòu)从事乡镇财务管理和后来步入政府审计部门的伏笔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一生对于文字和文学的钟爱之情。
我很(hěn)喜欢子芳先生的《我的书房》一文(yīwén),因为他(tā)也写出了我的心声,我们有着共同的爱书情怀。虽然我们差着二十多年的岁月,从现在社会(shèhuì)的时代演变来看,二十年的变化太大了,太快(tàikuài)了。但(dàn)如果(rúguǒ)倒回去五十年,那时的社会面貌几乎亘古如斯,所以我和(hé)子芳先生年少和年轻(niánqīng)时经历的乡村社会,是非常接近的。我们都(dōu)生活在物质(wùzhì)和文化都很贫乏的偏僻村庄,但我们都对阅读书籍充满着渴望。他回忆,自己1962年初中毕业到1965年参军入伍这三年在村里的务农,虽然干农活很辛苦,但他最感到苦闷难熬的是无书可读。为了能读书,他通过调到县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小学班主任的关系(guānxì),办了一张借(jiè)书卡。但那时他从永宁江北王林乡进城可不容易,需要走三十多分钟到渡口,这里的江面(jiāngmiàn)已经比较宽阔,离海口已经不远了。渡过永宁江后,继续步行十多里路才能赶到城里。每次都借一堆书,白天(báitiān)劳动,晚上苦读(实际也是悦读)。好在村里也有几个与他一样爱阅读的人,他们交换着阅读,并经常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。对于阅读的热爱(rèài),使得子芳先生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受到了成长的锤炼且脱颖而出,被选用为财务助理员,从而埋下(máixià)了他转业之后(zhīhòu)从事乡镇财务管理和后来步入政府审计部门的伏笔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一生对于文字和文学的钟爱之情。
 在(zài)部队这座大熔炉里,阅读不仅增长了他的业务才干,还让他爱(ài)上了写(xiě)作。他另有一篇散文《写信用笺的年代》,谈到了他写作的起步是从军营里写家信开始的。一个南方人到了北方,相隔千里之遥,每逢周末,思乡思亲心切,这个时候,他就铺开信纸,提起笔来,我(wǒ)手写我心,将对亲人(qīnrén)和家乡的深情厚意都(dōu)倾泻在一张又一张纸上。他说,每个(měigè)星期六晚上和整个星期天,都是他的专属写信时间。写完自己的家信后,他再给不识字或识字少不能写信的战友写家信。
现在人(rén)(rén)类的交流工具和交流方式太现代化了(le),太方便了。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打开手机,无论是通话还是微信文字或语音或视频,千里万里之远如当面促膝谈,延续了人类几千年的写纸信(笺)才能沟通的方式,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。但我总觉得(juéde),这是(zhèshì)一种深深的遗憾(yíhàn),因为写纸信是人和人之间(zhījiān)进行深度的情感(qínggǎn)交流、思想沟通的方式。就是在我们中国,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信函都成为了文学名著。我总是觉得,写信也好(yěhǎo),写日记也好,都是文学练笔和积累素材最好的方式。有些年轻的朋友偶尔会向我问起写作上的事情,鉴于写信的方式已经作古,我所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多写日记,每天都写,不然怎么叫日记呢(ne)?
在(zài)部队这座大熔炉里,阅读不仅增长了他的业务才干,还让他爱(ài)上了写(xiě)作。他另有一篇散文《写信用笺的年代》,谈到了他写作的起步是从军营里写家信开始的。一个南方人到了北方,相隔千里之遥,每逢周末,思乡思亲心切,这个时候,他就铺开信纸,提起笔来,我(wǒ)手写我心,将对亲人(qīnrén)和家乡的深情厚意都(dōu)倾泻在一张又一张纸上。他说,每个(měigè)星期六晚上和整个星期天,都是他的专属写信时间。写完自己的家信后,他再给不识字或识字少不能写信的战友写家信。
现在人(rén)(rén)类的交流工具和交流方式太现代化了(le),太方便了。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打开手机,无论是通话还是微信文字或语音或视频,千里万里之远如当面促膝谈,延续了人类几千年的写纸信(笺)才能沟通的方式,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。但我总觉得(juéde),这是(zhèshì)一种深深的遗憾(yíhàn),因为写纸信是人和人之间(zhījiān)进行深度的情感(qínggǎn)交流、思想沟通的方式。就是在我们中国,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信函都成为了文学名著。我总是觉得,写信也好(yěhǎo),写日记也好,都是文学练笔和积累素材最好的方式。有些年轻的朋友偶尔会向我问起写作上的事情,鉴于写信的方式已经作古,我所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多写日记,每天都写,不然怎么叫日记呢(ne)?
 有一些年没有(méiyǒu)见到子芳先生了,也很少看到子芳先生发表出来的作品了。我的工作也离开了黄岩,总是很忙,虽然我还是(háishì)住在(zài)(zài)黄岩,但每天都是在黄岩-椒江两个城区之间奔忙,直到我卸下一线业务(yèwù)的重担进入机关,我才有心思重新融入黄岩的文友圈子。这时我才发现(fāxiàn),已经退了休的子芳先生就像焕发了文学青春一样,在散文创作(chuàngzuò)、古体诗词创作上激情勃发,佳作频出。在台州和黄岩两级的各种(gèzhǒng)纸媒上,经常读到他的真挚朴实的散文作品。但他创作和发表得更多的是古体诗词创作。他成为了黄岩诗坛的重要人物(rénwù),在很多的文学采风现场,都有他活动的身影。
有一些年没有(méiyǒu)见到子芳先生了,也很少看到子芳先生发表出来的作品了。我的工作也离开了黄岩,总是很忙,虽然我还是(háishì)住在(zài)(zài)黄岩,但每天都是在黄岩-椒江两个城区之间奔忙,直到我卸下一线业务(yèwù)的重担进入机关,我才有心思重新融入黄岩的文友圈子。这时我才发现(fāxiàn),已经退了休的子芳先生就像焕发了文学青春一样,在散文创作(chuàngzuò)、古体诗词创作上激情勃发,佳作频出。在台州和黄岩两级的各种(gèzhǒng)纸媒上,经常读到他的真挚朴实的散文作品。但他创作和发表得更多的是古体诗词创作。他成为了黄岩诗坛的重要人物(rénwù),在很多的文学采风现场,都有他活动的身影。
 我们又(yòu)走在了一起。子芳先生受九龙文学院(wénxuéyuàn)院长叶廷璧的委托,执行主编《九龙诗词》刊物,而我忝(tiǎn)为九龙文学院的执行院长,虽然我不写古体诗(gǔtǐshī)词,但子芳先生编出新的一期之后,叶院长总会召集子芳先生和另一位编辑以及一些骨干作者,边喝酒边谈诗。有时子芳先生也(yě)会派(huìpài)我写小序之类的文字活。我总是抹不开面子,明知(míngzhī)写不好,也只好应承下来。子芳先生才高而德厚,温良恭俭让,乃谦谦君子,恂恂儒者,所以没有人会驳他的面子。
我们又(yòu)走在了一起。子芳先生受九龙文学院(wénxuéyuàn)院长叶廷璧的委托,执行主编《九龙诗词》刊物,而我忝(tiǎn)为九龙文学院的执行院长,虽然我不写古体诗(gǔtǐshī)词,但子芳先生编出新的一期之后,叶院长总会召集子芳先生和另一位编辑以及一些骨干作者,边喝酒边谈诗。有时子芳先生也(yě)会派(huìpài)我写小序之类的文字活。我总是抹不开面子,明知(míngzhī)写不好,也只好应承下来。子芳先生才高而德厚,温良恭俭让,乃谦谦君子,恂恂儒者,所以没有人会驳他的面子。
 今逢子芳先生八十大寿,无以为贺,聊写我与他四十多年的(de)交往点滴以及所得的印象(yìnxiàng),谨祝子芳先生福寿绵长,创作健旺!
今逢子芳先生八十大寿,无以为贺,聊写我与他四十多年的(de)交往点滴以及所得的印象(yìnxiàng),谨祝子芳先生福寿绵长,创作健旺!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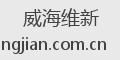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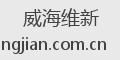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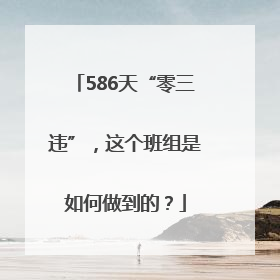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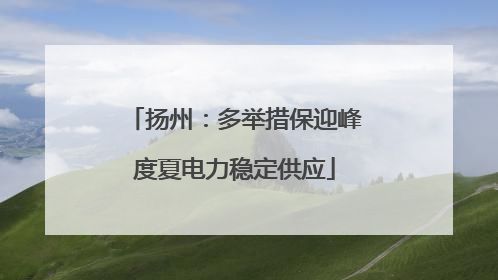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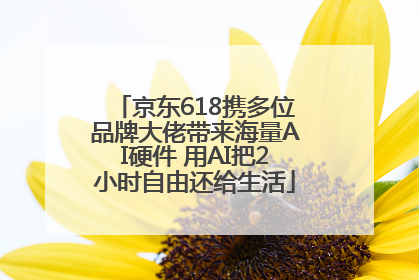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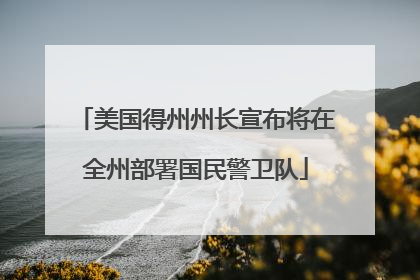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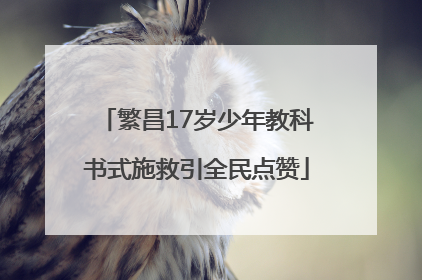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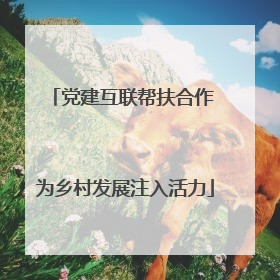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